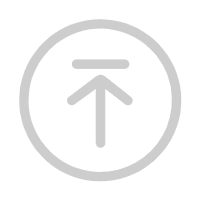《家乡博物馆》 [德]西格弗里德·伦茨 著 朱刘华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
■ 黄雪媛 yl12311线路检测德语系教师
每一个曾步入家乡博物馆的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体验,从喧哗街市来到博物馆内部,如同遁入一个无言的旧梦。凝视着先人使用过的日常器物、劳动工具、穿戴过的衣饰、供奉过的圣物、操练过的武器……一个人会忍不住想象自己的前生角色——铁匠铺的儿子还是织造匠的女儿?农庄的传人还是即将出征的兵士?展柜的证物们铺就了家乡既古老绵长又遗留大片空白的历史,观者不过是历史边缘和末端的偶然产物。也许在那一刻,我们不再骄傲自矜,而是被认祖归宗的严肃感和谦卑感包围,暂时放下了现实身份,顺服于博物馆传递出的宁静氛围——家乡博物馆就是这样一个奇特的所在。正如西格弗里德·伦茨在长篇代表作《家乡博物馆》中写到的:“更深远的过去征服了他们,他们直接忽视了其他的东西……收藏的物品传达并留下了一些影响,一种情绪,一种沉思,一场无言的反省。”
自我解救的唯一途径是讲述
中国读者最初是从长篇小说《德语课》认识这位世界级德语小说家的,而作家本人最重视的长篇却是1978年发表的《家乡博物馆》。2023年11月,在近半个世纪过去之后,《家乡博物馆》首个中文译本面世,这无疑是德语文学译介领域令人振奋的事件。德国读者喜欢把伦茨与君特·格拉斯作比较,正如中国读者倾向于把莫言与贾平凹归为乡土文学的两大代表一样。伦茨与格拉斯的家乡都位于从前的东普鲁士,一个在但泽,一个在马祖里地区,二战后都划归了波兰。两位作家在外形与爱好上也相似:喜爱抽烟斗,秋冬戴一顶瓜皮帽,连寿命也不相上下——都活到了88岁。当格拉斯抛出《但泽三部曲》致敬他的家乡,伦茨用一部《家乡博物馆》遥相呼应。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,格拉斯的叙事辽阔庞杂,生猛情欲与血腥暴力夹杂着但泽港的鱼腥味;而伦茨的叙事则绵密温厚,散发着禽舍、羊毛与染料作坊的气息。
伦茨说:“每个人都待在各自回忆编织的监狱里。”对于作家而言,自我解救的唯一途径是讲述,而讲述故土家园的故事是永不厌倦,常讲常新的,乡土故事与人类原始的爱欲密切相关,还跟对母亲的依恋有关,是故乡给了我们最初的味觉、嗅觉与色彩的记忆,是安全感和信任感的来源。与君特·格拉斯《铁皮鼓》的叙事手法如出一辙,伦茨的《家乡博物馆》采用了现实主义小说极为偏爱的第一人称倒叙手法:衰老的齐格蒙特·罗加拉——显然也是小说家自我的投影——躺在病床上,对后辈小伙马丁·韦特讲起了家乡博物馆的往事,开头即有惊人之语:“是我放了一把火……我别无选择,我必须毁了这里。”记忆的铁门一旦打开,封存的记忆便如蜂群般倾巢而出,一发不可收拾,最终成就了600多页的厚重长篇。
编织和拼接出的“记忆地毯”
但《家乡博物馆》绝不仅是伦茨对马祖里故乡的爱的宣言,它的“乡土文学”外壳包裹着一个政治与哲学反思的内核。伦茨借齐格蒙特之口,不厌其烦地记述童年印象:农场与集市、风物与食物、歌曲与舞蹈、赛事与节日,贯穿着家乡博物馆的建设史和搬迁史。两次世界大战并未真正摧毁齐格蒙特这位博物馆缔造者的信心,然而,当纳粹强权政治介入和征用博物馆时,齐格蒙特纵火销毁了亲手建设起来的一切,以决绝悲情的方式抵制纳粹法西斯主义对家乡博物馆的侵占和滥用。在四处肆虐的火舌中,地方史证物和证词灰飞烟灭,连同那些动物骨架和祖先圣骨、玩具娃娃与母子乐器、彩绘鸟类雕塑和亲手编织的蓝白色婚庆地毯,还有女儿心血凝成的《马祖里方言词汇汇编》,以及最为宝贵却已来不及抢救的织毯大师遗著《马祖里织毯艺术大纲》……故乡从此失去了记忆赖以依傍和储存的形体。在这个意义上,《家乡博物馆》是一曲故乡乌托邦的挽歌,也是一曲反纳粹悲歌。世上深情之人往往也会变成最“无情”之人,齐格蒙特就是这样一个“无情之人”,他给了故乡一个冷冷的背影:“做了断的人总要忍受痛苦,我别无选择。”
文学史不乏对“纵火”这桩人类最危险的罪孽之一的描述,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个叫“黑若斯达特斯”的古希腊年轻人,他纵火烧毁供奉着阿尔忒弥斯女神的亚底米神庙,只图千古留名,为此不惜付出死刑的代价;罗马皇帝尼禄为了打造一个崭新的、符合他心意的罗马城,派手下纵火焚城,皇帝本人则悠然登上塔楼,在七弦琴的音乐声中观赏着城中美丽的火海;三岛由纪夫借小说《金阁寺》探讨纵火案背后的犯罪动机,是否是“丑”对“美”的报复;而伦茨让齐格蒙特通过绵绵回忆,为纵火行为展开漫长的辩白,作家也借此对Heimat(故乡)——这个多愁善感又沉重复杂的德语词——进行了语义学的解读和历史学的审视。
我们不必诟病齐格蒙特的话风如此不同于现实中的口述,小说家不过是借了一个虚构的倾听对象,把语言的经线与纬线投入马祖里方言染缸里,染出最鲜明的颜色,然后一小块一小块地编织和拼接出家乡博物馆的“记忆地毯”。小说行文中时不时冒出的对于中文读者而言略显矫情的“哦,亲爱的马丁·韦特”,不过是在提醒读者:此处的回忆要另起一个头,或另排一条线了。“织毯”是《家乡博物馆》最吸引人的意象之一。织毯的纹理凝聚了似水光阴,图案在日复一日的编织中渐渐清晰,古老的爱意与想象得以赋形。伦茨赋予他的主人公“最伟大最杰出的织毯大师索尼娅·图尔克”唯一弟子的身份,使他身怀绝技,能够编织出复杂精美、独一无二的地毯和挂毯。“齐格蒙特,永远记住,你必须将事物本身自带的特性留给它们自己,什么也不能取代羊毛的柔软与温暖。”在白雪皑皑的冬日荒原的背景里,在战争带来的流离失所中,织毯给马祖里人温暖的依靠,而跨越种族和文化的工匠激情也深深触动着读者。
遗忘是“变回愚蠢”
小说人物群像里尤其耐人寻味的角色是亚当叔叔。这位马祖里家乡协会主席和乡土学学者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德国“乡贤”。他热衷于研究家乡的过往,痴迷于收藏一切有地方史价值的证物,“收藏的狂热让人胆大无边,你永远不知道他封钉在箱子里的是什么”。对于亚当叔叔而言,“当下”的价值只在于提供一个回望的平台和挖掘的起点,只有“过往”才是清晰可靠的,值得追寻和依恋的。亚当叔叔的住所是天然的家乡博物馆,他让文物为自己所处的时代、也为自己的存在意义说话。小说中有个情节,亚当叔叔为一群少年学生讲解藏品,孩子们对莫名其妙的古老物件无动于衷,听得百无聊赖,开始各种捣蛋。亚当叔叔却丝毫不恼火,讲述的热情反而愈加高涨,因为他相信,只有不为周遭所动的全情投入才能引起孩子们的兴趣,带去启发。

齐格蒙特在战争中失去了父亲,又被不近人情的爷爷赶出家园,后来被外冷内热的亚当叔叔收留。经年累月的耳濡目染,使齐格蒙特爱上了家乡的过往,他用小小的刮铲在土地里挖掘家乡久远的过去,像“勤劳的鼹鼠”寻找甲虫一样收藏关于家乡的种种“记忆”。不出所料,齐格蒙特成为了亚当叔叔的得力助手,长大后接过亚当的衣钵,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家乡博物馆的缔造者和建设者。“我很早就发现了归属感带来的满足,一切都很熟悉,没有。当我将第一样东西拿进我们的博物馆里时,第一个我自己拿来的文物,它让亚当叔叔那么兴奋,他将他偏爱的一个位置给了它,当时我觉得像是经历了一场毕业考试。”
齐格蒙特拿来的不是什么金贵的物件,而是一顶用未脱粒的、长度不一的麦秸秆编织而成的草帽。无论是旧草帽,还是一根带花纹的擀面杖,或者一个古老的黄油搅拌器——寻常物件在博物馆的空间内获得了历史的光泽,映现出往昔生活的神秘景象。“家乡博物馆”的证物以一种随意的方式被安置,而不是笼罩在意识形态的主题强光照射下,这是真正意义上的“纯真博物馆”:它抵抗遗忘,也拒绝被刻意展示和过度阐释。“许多东西都在那里待命,像是为了预期的辩护做好了准备。”在建立博物馆的那些年里,齐格蒙特和亚当叔叔一样,怀抱着同样的热忱,也被同样的信念鼓舞着。“这个信念来源于马祖里,这片黑暗、神秘的土地只有在无人记起的时候才会被彻底抛弃,才会真正意义上消失在这个世界上。”遗忘是什么?按照马祖里的方言,是“变回愚蠢”(zurueckdummen)。“遗忘是一种疾病,一旦患上就无法阻挡,没有药物可以帮助。”假如说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是个人与家庭最难承受的痛苦,那么患上文化失忆症则是一个族群最大的悲剧。
记忆和遗忘的博弈时时都在发生,并且在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身上悄悄发生着。不管我们如何挣脱身上的历史烙印,远古时代一直在悄悄支配着我们,直抵心灵深处;乡土记忆和族人面孔召唤着我们对于自我身份的溯源与认同。尽管《家乡博物馆》的中译本姗姗来迟,但在2024年阅读这部小说也许恰逢其时:在一个逐渐呈现“去全球化”趋势、重新强调“本土化”的时代里,《家乡博物馆》会促使读者思考何为真正的故土之爱和祖国之爱;重新审视历史与现实、本土与世界、过去与未来的哲学和政治关联。2024年,是时候把眼睛和心灵重新投入到长篇小说的深河里,摆脱碎片化阅读带来的浮浅。
当我读完整部小说,再次回到第一章节,我的目光停留在一小段文字上:“当博物馆着火的时候,正巧有两艘渔船驶过埃根隆德,船上的人显然不想留意这场火灾,渔船穿过浓烟和漆黑的灰烬,轻盈地驶向了入海口。”我想,也许伦茨是在暗示记忆与遗忘的辩证法:同一个世界,人却活在不同的时空体系里,每个人必须承担各自的记忆,承受各自的命运;然而,我更愿意把它解读为:渔船摆脱了大陆的沉重,驶向广阔的大海,如同一个人卸下记忆的重负,轻装上路。